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内涵特征与评价体系
作者杜德斌 祝 影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对其内涵的认识首先要从相近概念的历史溯源开始,只有在基本的理论范畴上明确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内涵、功能、特征,廓清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评价维度和评价体系,才能在实践中更加准确地把握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点与关键。

本世纪以来,知识化与全球化迅猛发展,两者互为因果,又互相促进。这两大趋势正在重塑世界城市功能,重构全球科技和经济版图,加速形成全球创新网络(GIN)。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全球创新网络中的枢纽性节点城市,代表着所在国家在世界分工体系中所能达到的最大高度。当前,世界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叠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塑,但大国间的科技竞争更加激烈,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战场。积极谋划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成为许多国家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挑战和增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在中国加速崛起和科技创新实力加快提升的过程中,上海、北京、深圳等中心城市因其产业基础相对雄厚或创新环境相对优越而成为全国科技创新的龙头,具备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为建设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21年3月,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支持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这表明中国在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实践方面已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概念源起与内涵界定
关于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及相关概念的讨论包含了国家和城市两个层面的含义。从国际上看,关于国家层面的相关概念,最早可追溯到1959年英国学者贝尔纳提出的“世界科学活动中心”。之后,1962年日本神户大学科学史家汤浅光朝用定量化的成果指标来界定“科学活动中心”的范畴,认为当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段内的科学成果数超过全世界科学成果总数的25%,则该国在此时段内就成为世界科学中心,该国保持为世界科学中心的时段为其科学兴隆期。这些概念和提法被国内外许多学者引用或加以延伸,相继提出世界科学中心、世界科技中心等概念。就其本质而言,这些概念和提法所描述的都是不同时期科技创新活动在世界范围内的空间非均衡分布问题。当时,世界科技中心或世界科学中心都是以“单极”的形式出现的。从空间属性来看,它们所关注的空间单元通常落在国家层面,指在特定时期科技领先的国家,如14—15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18—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法国和德国以及20世纪以来的美国等。
关于城市层面的相关概念始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硅谷、波士顿、赫尔辛基和班加罗尔等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技活动中心或新兴产业中心的异军突起,学者们对科技活动空间异质性问题的关注开始逐步从国家层面下移到次国家(sub-national)的区域或城市层面,因此提出了创新中心城市、创新枢纽区域等相关概念。在国际上,《在线》杂志在2000年最早提出了“全球技术创新中心”的概念,并评选出46个全球技术创新中心。联合国《2001年人类发展报告》对该项成果进行了评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技术成长中心”的概念,指众多研究机构、创业型企业和风险投资集聚在一起的地区。澳大利亚智库研究机构2thinknow发布的《全球最具创新力城市排行榜》,从文化资产、基础设施和市场三大维度界定创新城市。
在国内,2000年后学术界先后提出国际产业研发中心 [1]、产业研发枢纽 [2]、科技创新城市 [3]、国际研发城市等相近概念。这些概念从不同角度反映出全球创新活动发展的新趋势及其空间集聚特征,对定义“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与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内涵存在较大差别。2014年杜德斌最早提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概念,将“科技创新中心”定义为科技创新资源集中、科技创新活动集中、科技创新实力雄厚、科技成果辐射范围广,从而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挥价值增值功能并占据领导和支配地位的城市或地区 [4]。当一个城市的科技创新活动的影响波及全球,成为引领世界科技—产业范式变革的源头之时,就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 [5]。
基本功能与派生功能
从根本上说,科技创新是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功能。从社会活动来说,科技创新包含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创新三个过程。而就其对社会的作用或功能来说,科技创新则指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各个领域。因此,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主要功能应至少涵盖四大方面: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产业驱动和文化引领 [6-7]。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是科技创新中心的两大基本功能,产业驱动和文化引领则是其两大派生功能。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四大功能具有由核心向外延不断推进和升华的内在逻辑关系。
科学研究功能是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形成的基础条件。创新资源在空间上的高度集聚和产学研的高度一体化使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往往成为世界上创新氛围最浓厚、创新生态最适宜的区域。这里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不仅有着全球顶尖科学家和国际一流科研团队,还拥有先进的科研基础设施、研究平台以及持续稳定的基础性投入,集人才培养与知识创新功能为一体,因此成为世界新知识和新思想产生的重要源地,是世界重要的科学研究中心。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作为世界科学研究的主阵地,具有如下典型特征:其一,科研实力强大,拥有一批划时代意义的科学成果;科研设施设备一流,在国际大科学项目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二,高端人才汇聚,拥有全球顶尖的科研领军人物和国际一流水平的科研团队,且其领先的研究水平还会吸引世界各地优秀人才云集,并形成良性循环。其三,具有良好的学术氛围,研究领域往往处于世界相关学科和技术领域的最高端,代表科学研究的国际前沿,引领当代科技或学科的发展,并不断衍生新的学科领域或方向 [6-7]。
技术创新功能是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成长的关键环节。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作为各种技术创新要素集聚的高地,汇聚了全球技术、人才、信息、资金等优质创新资源,在众多跨国公司以及本地创新企业的推动下,成为全球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的创新发展增长极。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作为全球技术创新的策源地,具有如下典型特征:其一,集聚了大量世界顶级的科技企业和企业研发中心,新创(startup)和中小科技企业活跃。例如,硅谷云集了7000多家高新技术公司的总部,其中世界排名前100家高新技术公司总部达到20%。其二,具有良好创新创业文化氛围,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多样化的创新人才,包括具有创新精神的创业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创新管理人才和风险投资者等。其三,创新投入和产出高。拥有较高的创新投入规模(如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和研发人员规模),同时具有相应较高的创新产出(如专利总量、高新技术产业产值),是众多新技术、新产品的发源地,世界产业变革的策源地。
产业驱动功能是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发展的根本目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强大的知识生产和技术创新功能,决定了其在全球产业范式变革中的主导地位。驱动产业发展既是科技创新活动的出发点,也是其目的和归宿。其一,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产生出的新知识、新技术能够催生新的产业部门。技术进步改变要素组合模式,导致分工深化、产业迂回度提高、中间环节增加、附加价值增大,不断形成新产品、新产业和新业态。良好的科技、教育环境和适宜科技创新的文化、创新制度催生出大量的新创企业,推动科技产业的发展,使其成为世界新产业的发源地。其二,新技术、新工艺能够改造传统产业,驱动产业组织模式的升级转型。新技术在创立新的产业及其部门的同时,也必然要求对原有的产业及其部门进行改造,赋予传统产业以新的内涵和面貌。这包括传统产业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组织结构以及管理结构的升级。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基本功能与派生功能
文化引领是科技和经济发展的最终结果,也是科技创新中心发展的最高境界。作为时代先进生产范式的代表,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对世界文化的形成有着引领、示范和塑造的作用。首先,科技创新中心拥有最具包容性的创造性文化,其中隐含的人本主义理念赋予了这种文化以超强道德感召力,使这种文化成为具有某种时代性、进步性特征的先进文化。其次,科技创新的灵魂在于科学文化,而科学文化构成了世界先进文化的基石与先导。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形成了先进文化的基础框架,科学的创新理念、价值取向代表了先进文化的活跃前沿。最后,科学技术不断塑造人类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实践的变革必然重构时代主流价值观。任何重大技术变革都会通过影响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塑造着代表那个时代的创新精神、商业理念和消费时尚,从而引导人类价值观的嬗变和思想体系的演进。总之,全球科技创新中心通过在制度领域发展国家创新系统,在价值领域倡导求变精神,在生活领域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从而深深地浸润和濡染人的心灵。
网络特性与具体特征
根据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内涵与功能以及世界主要科技创新中心城市发展的实践,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可概括为五个主要特征:功能支配性、结构层次性、空间集聚性、产业高端性和文化包容性。其中,功能支配性与结构层次性源于全球创新网络的网络属性,而具体则呈现出空间集聚、产业高端和文化包容的共性特征。
功能支配性特征体现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全球创新要素集聚最多、创新要素质量最高的城市,具备强大的知识、技术生产能力和输出能力。它向全球范围提供技术和产品的输出以及研发服务,是全球创新网络中技术、信息、人才、资本的联系与流动的重要枢纽。占据全球创新网络最高的结构地位,其对全球创新资源流动具有强大的引导、组织和控制能力,能支配全球创新资源的流动方向。同时,因为集聚了大量的跨国公司总部、研发总部和区域性研发总部,通过对全球价值链中的高端研发与设计环节的掌控,主导着全球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发展方向,并且能够通过海外研发活动,全方位整合利用全球创新资源,控制全球资金技术、人才和信息等创新要素流动方向,支配全球研发创新资源的空间配置格局。换言之,它不仅是“创新要素池”,而且还是创新要素流动的“控制阀” [6-7]。
结构层次性特征体现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等级性和差异性。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因为汇聚众多高质量创新要素而成为创新能量巨大的“场源”,以各种创新要素流的流出与流入完成不同节点之间的能量交换,辐射和影响着全球市场。这些不同的场源之间存在一定的力量关系,从而造就了全球创新网络节点间的结构等级性。具体表现为不同等级的节点城市具有不同的支配地位,包括控制地位和从属地位。处于控制地位的节点城市,具有较高的创新能级,对外科技辐射范围广,创新要素输出规模大于流入规模;处于从属地位的节点城市,创新能级相对较低,对外科技辐射范围有限,创新要素输入规模大于输出规模。在功能上,高等级与低等级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之间存在一定的分工。如在信息产业领域,美国硅谷掌握着信息产业的核心技术和标准,控制着产业链上游的芯片设计,而中国台湾、印度的班加罗尔等则掌握着产业中游的技术,承担着集成电路的代工以及软件产业上游产品分解后的子模块开发和独立的嵌入式软件开发等技术。
空间集聚性特征体现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聚集度和共生性。在城市层面上,科技企业、大学与科研机构的空间分布具有群聚的倾向,往往在城市内部特定区域形成创新机构相对集中的创新集群。因受技术和知识溢出的地理邻近性规律支配,创新企业和机构倾向于以集群的形式存在,特别是具有产业关联性的上下游企业。在各种创新主体中,由于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处于科技创新的源头,是科学研究重镇和人才培养的摇篮。因此,许多城市的创新产业集群都是以大学为核心发展起来的,如美国硅谷、波士顿、北卡研究三角园区等。在区域层面上,存在多个科技创新城市彼此共生、腹地交互重叠的现象。与金融中心在区域上的排他性不同,同一区域内可能形成多个科技创新中心,相互之间存在着某种良性的互动和学习关系。
产业高端性特征体现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先进性和高级化。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技术先进性决定了其产业形态“高端化”和产业结构“高新化”的特征。其一,产业形态的“高端化”,指通过技术革新,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使产业处于价值链高端,具有高附加值的特征。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看,科技创新中心以高智力人力资本要素参与国际分工,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占据以高科技、高附加值、高智力密集性为特征的产业链“高端”节点。这些产业的高智力投入,易保密、难模仿的技术优势以及低竞争性的市场结构,造就了这些环节的高附加值和报酬递增的特征。例如,德国从工业1.0到工业4.0的演进过程中,依靠技术革新,不断推动制造业去低端化,保持着高端制造业竞争优势,始终盘踞在制造业产业链中的高附加值环节。其二,产业结构的“高新化”,指城市不断催生出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方向演进,始终以技术(知识)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例如美国硅谷,从20世纪50—60年代的国防工业,60—70年代的集成电路产业,70—90年代的个人电脑产业,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IT产业,再到近年来异军突起的生物医药产业和新能源产业,始终以高新技术产业主导和引领全球产业结构的变革。
文化包容性特征体现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活跃度和多元化。创新的原动力不仅来自科技,更来自文化。文化是孕育科技创新中心的母体,真正具有创新力的城市一定具有深厚的文化土壤,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高度信任的文化特质。从美国的硅谷、纽约到以色列的特拉维夫等创新城市的发展经验来看,它们均具有宽容失败、崇尚冒险、包容异质思维、激励草根精神的创新创业文化氛围,“人人创新”、“草根创业”成为区域发展最为重要的文化基因。比如,硅谷具有典型的包容性文化氛围,一方面体现在文化的多元性和对异己的包容,吸纳了来自全球的不同文化背景的多样化人才与精英;另一方面体现在对失败的宽容,最大限度地尊重人、激发人的创新激情与活力,从而促进初创公司繁衍和高水平创新成果产生。
评价体系与全球排名
国际上有关“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并无完全统一、权威的评价标准。目前国外比较可靠且连续发布的有《机遇之都》(Cities of Opportunity)评价中的“创新机遇”指标、全球城市实力指数中的“城市研发”指标以及“全球创新城市”指标。其中,普华永道《机遇之都》自2007年始,2016年第七版之后未再更新。日本森纪念财团城市战略研究院的《全球城市实力指数》(Global Power City Index)始于2008年,但研发只是其中一个维度,并非专题的全球创新城市评价。目前,澳大利亚智库研究机构2thinknow的 《城市创新指数》(Innovation City Index)是覆盖面最广且聚焦于创新的全球创新城市评价,自2007年起每年发布,至今已涵盖500个基准城市162个指标。这 162个指标分成文化资产、基础设施、市场三个大类,文化资产用以测度可衡量的思想,基础设施测度实施创新的软硬设施,市场测度城市在全球市场中的实力和联系、创新的基本条件和联系、创新的沟通交流,三大类之下又分为31个分项。
全球创新城市虽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但其内涵相对接近, 在其划分的四个城市等级:第一等级支配型(NEXUS)、第二等级枢纽型(HUB)、第三等级节点型(NODE)、第四等级潜力型(UPSTART)中,支配型和枢纽型可以认为是对全球创新格局起着支配和枢纽地位的全球性创新城市。根据2021年2thinknow的最新排名,第一等级支配型有38个城市,第二等级枢纽型有61个城市,前两个等级共有99个城市,分别属于27个国家或地区。其中,54个是美国城市,占据前两个等级城市的54.5%,再次佐证了美国当之无愧的世界创新霸主地位,其中波士顿、纽约位列前茅;中国(不含台湾地区)和澳大利亚以5个城市并列第二,上海、北京、深圳、悉尼、墨尔本属于支配型城市,香港、广州、布里斯班、珀斯、堪培拉属于枢纽型城市;日本上榜城市有4个,东京和大阪属于支配型城市,京都和名古屋属于枢纽型城市;德国有3个城市上榜,柏林列入第一等级,慕尼黑和汉堡列入第二等级;加拿大、意大利、西班牙、荷兰、韩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各有2个城市上榜。除美国外,中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在全球创新城市中表现突出。

近年来,国内对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各类评价日渐增多,《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评估报告》由上海经济信息中心课题组自2018年起发布,以全球近150个主要创新城市或都市圈为评估对象,从基础研究、产业技术、创新经济和创新环境四大维度重点展示和分析综合评分前100名的城市;《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指数》由施普林格·自然联合研究团队和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在2020年首次发布,构建了科学中心、创新高地、创新生态3个一级指标12个二级指标,在全球范围内遴选 30 个各具特色的城市(都市圈)进行评估。与国外“全球创新城市指数”相比,这两个评价体系偏重于科技创新投入产出指标,对效益的可持续性关注度不足,同时作为对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评价,缺少辐射带动力、全球影响力等指标。
我们认为,一方面,创新能力是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最基本最核心的构成要素,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必然拥有最强大城市创新能力,对城市创新能力的评价是评价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基础;另一方面,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全球创新要素的聚集地和全球创新网络的枢纽型节点,当一个城市的科技创新活动的影响波及全球才能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强调全球影响力和辐射力的全球城市评价对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评价有所启示。在此基础上,由于科技创新中心城市显示出越来越多创新生态系统特征,对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评价也需要更加注重生态论和系统性的内在特质,在实践中转向对系统耦合协同程度的评价 [8]。
杜德斌,教授;祝影,客座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全球创新与发展研究院 ,上海,200062。
Du Debin,Professor; Zhu Ying, Guest Researcher: Institute for Glob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1] 杜德斌, 张仁开, 祝影, 等. 上海创建国际产业研发中心的战略研究.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5, 4: 23-29.
[2] 王铮, 杨念, 何琼, 等. IT产业研发枢纽形成条件研究及其应用. 地理研究, 2007, 26(4): 651-661.
[3] 胡晓辉, 杜德斌. 科技创新城市的功能内涵、评价体系及判定标准. 经济地理, 2011, 31(10): 1625-1650.
[4] 杜德斌. 上海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路线图及实施建议. 上海综合经济, 2014, 9: 1-10.
[5] 杜德斌. 上海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路径. 科学发展, 2015, 1: 93-97.
[6] 杜德斌.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 动力与模式.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7] 杜德斌, 何舜辉.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内涵、功能与组织结构. 中国科技论坛, 2016, 2: 10-15.
[8] 祝影, 唐春光, 孙锐,等. 基于系统耦合的中国科技创新城市评价. 科技管理研究, 2019, 39(24): 30-39.
关键词:全球科技创新中心 内涵 功能 特征 评价体系 ■
相关阅读
-

Zhu Ying, Guest Researcher: Institute for Glob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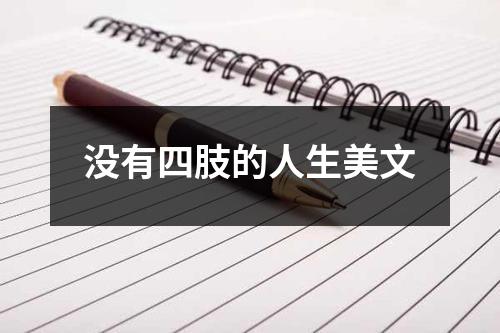
“bigBooooM”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8篇没有四肢的人生美文,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后的没有四肢的人生美文,供大家阅读参考。篇1:没有四肢的人生美文 没有四肢的人生美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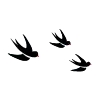
海关依法对出入境交通工具、人员、物品(包括货物、行李、邮包)等进行监管,肩负防控重大传染病、动植物疫情跨境传播,防范外来物种入侵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使命...
-

现在,大家都生存在一个极速发展的社会,一切东西,都以快为标准,车速度要快,肉食动物要长得快,大家都忙成了陀螺。作为社会关系的单位-家庭,在这个社...
-

人生下半场,最好的活法,不是事事如意,而是具备这4种智慧,看淡,看开,智慧,洞察力,事事如意,内心深处,人生下半场...
-
劳动创造幸福的时代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劳动创造幸福的系列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劳动幸福观在新的历史发展方位下的创新发展,以人民幸福为价值旨归和核心内容,致力于为人类谋幸福...
-
小编整理了梦想让生活更美好(6)作文,用文字来表述人物,感受描绘生动的人物形象。如何写好作文,平时的阅读和积累好句,十分的关键。...
-

提及到性冷淡疾病,有很多的已婚人士特别困扰,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有可能出现该病的症状,给身体健康带来不利的影响,还会波及到夫妻间的感情,...
-

【原创】深圳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关口前移、系统防控 构筑动物防疫安全屏障
处理猪肉不小心可能感染猪链球菌病,遇到流浪动物或受伤的禽鸟处理不当易传染疾病。近年来,随着非典、埃博拉、禽流感等人兽共患病的频发,人兽共患病关系兽医生物安全...
-

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 加强生物安全领域立法 筑牢国家安全法治屏障
河南人大网是由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主办、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大河网络传媒集团协办的河南省人大常委会门户网站,设有“人大概览、人大要闻、履职动态、代表园地、智慧人大”等多个板块...
-

二周岁以下的子女,一般随母亲生活,父母双方协商由父亲直接抚养的除外。因为未满二周岁的子女,对母亲生理上的需求、心理上的依赖,是父亲所不能替代的。加之母亲更耐心、细致...
发表评论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请发送邮件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